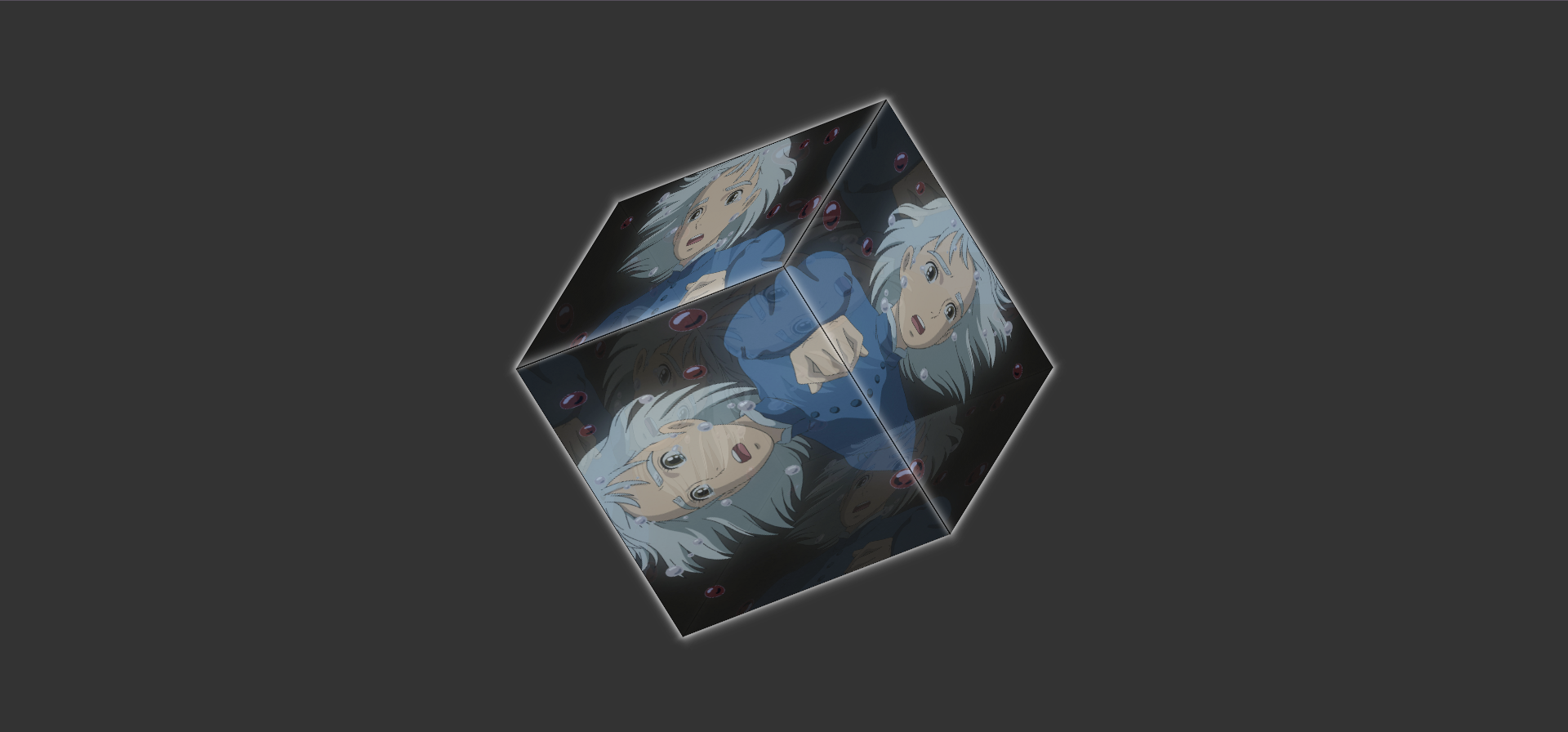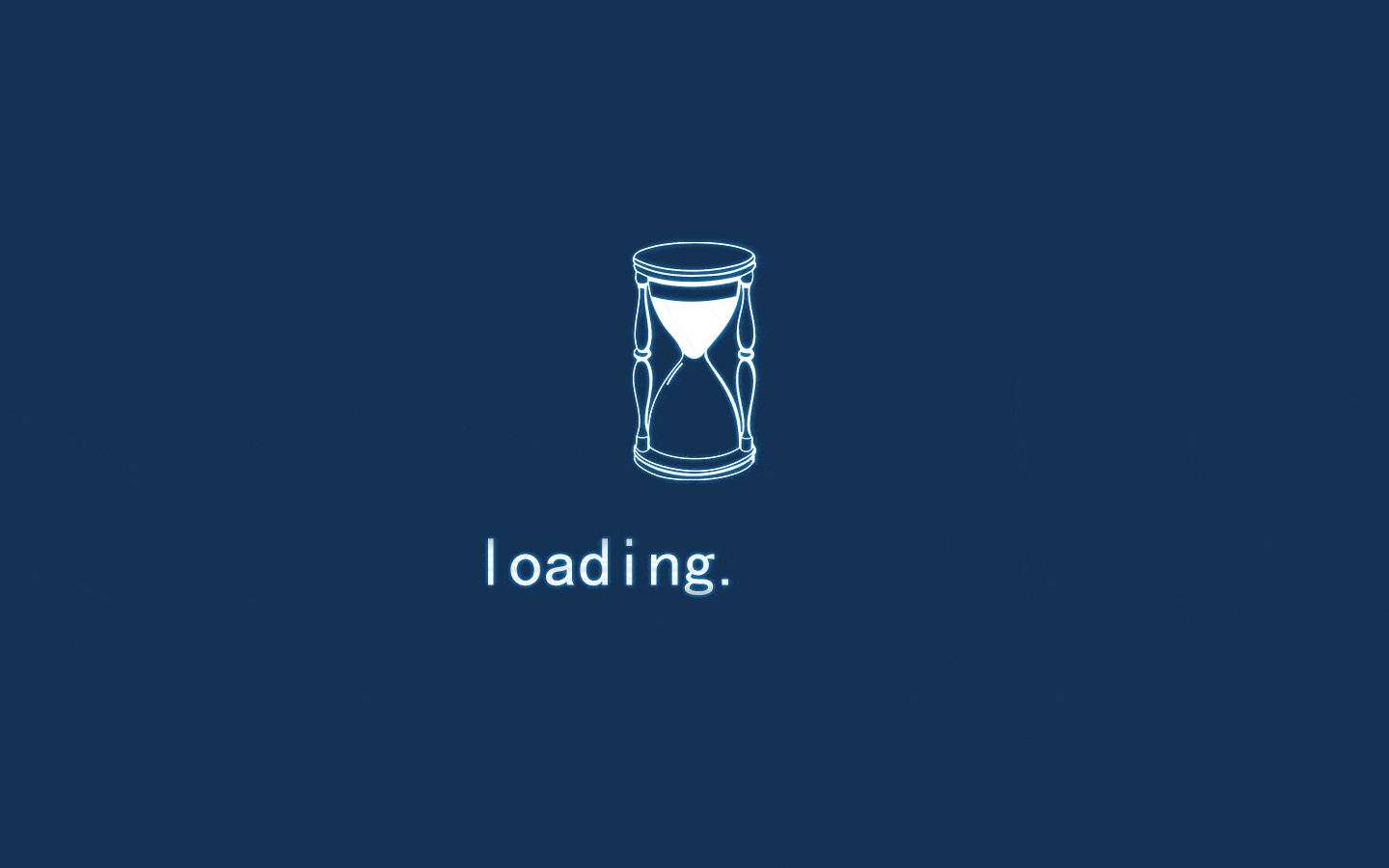松本清张
一个秋天的晚上,六十二岁的放债者,在家里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敲扁了脑壳致死。凶手偷了一只银箱逃掉了。银箱里有二十二张债据。凶手从中偷走五张后,把银箱丢在附近的池塘里。被谋杀的放债者住在东京西郊一幢房子里,当时那里几乎一半是农田。
嫌疑犯上木寅郎被捕,他声称没钱请律师,于是年轻的原岛直见律师被指派为他免费辩护。原岛详细地阅读了本案的调查报告,了解到以下事实:被害者山岸神原先拥有大片农田,十年前卖给一个房地产经纪人。用这笔收入,他造了一幢二层楼住宅,并做起小规模的金融事业。当他被谋杀时,妻子已去世三年,没有子女。他单身过日子,把二楼租给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及其妻子,房租不高。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贪婪的人,为什么会收低房租呢?因为他知道这个教师是二级黑腰带柔道手,住进他家就既是房客又是保嫖。
10月15日,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得知母亲病重垂危,偕妻子当天启程回故乡九州岛。谋杀案发生在10月18日,山岸的尸体于19日上午被一个来还债的邻居发现。
他报了警。
验尸官的报告里说,死因是脑部被人从后面敲扁,造成脑震荡并大量内出血。
致命的伤口有成年人的巴掌大。受害者倒地后用手脚爬行几步身亡。胃里剩余物化验结果显示,山岸死于晚饭后三小时左右。习惯于自己做饭的山岸一般在6点30分吃晚饭,这说明谋杀案发生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。
房间里没有被搞乱的迹象。显然是山岸自己为凶手开门的。门被一根相当粗的门闩闩住,不可能从外面打开。当尸体被发现时,门闩搁在门旁,只能是山岸本人拿掉门闩的。肯定有一个山岸认识的人来造访。
邻居都没有听到过敲门或喊叫开门声。卧室角落里有电话,凶手可能打电话说要来访,山岸起床拿掉门闩等着他。他一定和来访者很熟悉,没想到这个人要来谋杀他。
存放债据的银箱被盗,与凶手也有关联。凶手肯定知道银箱存放在什么地方,里面有些什么东西。他的企图是为了偷去债据;而在一座佛像下面,警探发现有十五万日元的现钞,却安然无恙,没有踪迹表明凶手曾经试图找到这笔巨款。
案发两天后,警方逮捕了上木寅郎。在调查中,有位中村吉屋先生说那天晚上从家中浴室窗口,看到一个人走向山岸家,这个人很像在火车站附近开面馆的上木寅郎。上木寅郎三年前在火车站隔壁开了一家面馆。结果,生意并不红火,顾客越来越少,面馆亏本,背上一大笔债,他陷入了困境。这个上木寅郎,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时曾在市区一家旧书店当过营业员,做面馆生意完全外行。现在糟了,欠山岸的利息已四倍于他借的钱。到谋杀案发生时,上木共欠山岸七百五十万日元。山岸讨债时冷酷无情,他知道上木永远还不了债,打算把上木抵押的地皮和店铺占为己有。上木恨透了,曾经在一些人面前扬言说:“我要杀死这个老家伙!”
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。屋里指纹很多,但已被抹得模糊不清。楼上有清晰的指纹,是两名房客的,他们在案发前三天回九州岛了,足以证明不在现场。
余下的一些指纹也许是山岸其他债务人的,都旧了。
凶手没有留下凶器。警方没找到可疑的脚印。门闩可能是凶器,可是与那致命的伤口相比较,既不够粗,也不够重。门闩上的指纹是山岸本人的。山岸几乎秃顶,伤口往外流血不多,门闩上没有头发或血迹。
但在房子后面屋檐下有一堆松木柴,是烧火用的。当时煤气管还没接到这个地区,有许多人家用液化煤气罐,但山岸由于吝啬和习惯于农村生活,他仍用木柴烧炉子做饭菜。松木柴堆成好几层,看来用这木柴作凶器要猛击好几下才能造成山岸头上那样的伤口。木柴表面粗糙不平,很难找到指纹,而且也不可能留下头发或血迹。
了解了以上情况,原岛开始看上木的供词:“大概两年前,我从山岸处借到钱,利息可恶地高。从此我因欠债而受尽折磨。
最近他威胁我说,要把我抵押的店铺和地皮拍卖掉。生意的失败和山岸的逼债使我绝望。我决定与妻子和孩子一起自杀;但是,天哪!这岂不是便宜了那个老家伙吗?
在我死以前,非先杀死他不可。这至少也算是为其他受他折磨而痛苦的人做件好事。
“10月18日,我在离火车站约两百米的万园麻将馆,从傍晚约7点开始打麻将,同桌有三个朋友,中田、前田和西川。我们打了三圈,柴田来看我们打牌。他也想打,我就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,让他坐在我位子上打。他很高兴。我离开了麻将馆,时间也许是9点。”
“但是我没有回家,我在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,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,我已经弄到了两百万元,带在身边,马上到他家去。他听到我有这么多钱了,一口答应我到他家去,甚至用迫不及待的口气,说他先开好门等我。”
“果然是山岸为我先开好门。我知道教师夫妻三四天前回九州岛去了。教师到我店里吃面条时,曾亲自告诉过我。”
“在我进门前,我转到房子后面,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柴堆,就去拿了一根木柴,藏在背后。”
“山岸引我到客厅,从墙角里一堆坐垫上面拿了两只,放在一张桌子旁。我坐下时赶紧把木柴藏到坐垫下面,我说我带两百万日元来了,请他给我写收据。说着,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,其实里面包的是废纸。他一看以为是钞票,高兴得跳起来,走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。”
“我想时机已到,也跳起来跟他进去,从背后用木柴猛击他的头部。他脸朝下倒在地上。我弯身再在他后脑打了三下,他没有动静了。为了让人认为是盗贼而不是来客作案,我把两只坐垫放回原处,然后在这间房里寻找银箱,在壁橱里找到了。我要撕掉我借他的债据,可是不懂得怎样打开那把数字锁,决定把银箱带走。出门以后,我到屋后把木柴放回柴堆上,不记得放在柴堆的什么地方了。整个经过大约半个小时。”
“月亮升起了,我走到路边草地里,找到一块石头,砸开了银箱。借着微弱的月光,我把有我名字的债据放到口袋里,然后把银箱丢进右面的池塘里。我走到不远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,拿出口袋里所有债据,点了一根火柴就全把它们烧成了灰,随即用脚把地上的灰抹掉。”
“当警方告诉我说,银箱已被找到,我的债据仍在箱里,我真的感到很惊奇。在山岸的账薄里有一个债务人的名字和我的很相似,警方以为我搞错了,在黑暗中误以为这个人的债据是我的。我烧掉了他的债据,因此他的债据不在警方找到的银箱里了。由于当时我很兴奋,很可能出这样的错。”
“回到麻将馆,四个朋友仍在打麻将。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,等柴田‘胡’了,我换他的位子,打了一圈。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。如果我说出来也会很镇静的,因为我杀死山岸神没有负罪感。”
“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好,债据被我烧了。山岸没有继承人,谁欠他的债全一笔勾销了。我感到快乐和轻松。”
原岛看完后,感到本案果然简单。他所要做的,只有请求对被告从轻发落;然而,又有一份材料使他大出意料。上木在公诉人面前翻供了,说警方对他搞逼供,还进行诱供。
上木寅郎对公诉人说:“我说我和中田、前田和西川在万园麻将馆打牌,打了三圈我让给柴田打。我到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,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。他说他起床等我去。以上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至于其他我在警察局里说的则都不是真话。
“我在电话里没有对山岸说我已经弄到两百万日元。我怎么也弄不到这么多钱;可是警方坚持说,如果我不说带钱去,山岸不会起床等我。他们说,如果我只说要去见他,他一定会叫我明天去。他们说我把一包看起来像一捆钞票的纸包放在口袋里,然后到山岸家去。我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思。的确,根据山岸的为人,任何第三者都会同意警方的说法,因此我承认他们是对的。实际上,我对山岸说我有办法还债,想跟他商量。他说他愿意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办法,才同意我去,并先开好门等我去。”
“于是我走到他房子那里,但不能进去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办法。我真怕失去我的店铺和地皮,只想要求他耐心等待我还债。我知道这只会使他大发脾气。我不敢面对他,因此我没有进屋去,只在屋外徘徊了半小时左右就往回走了。”
“回到麻将馆接柴田的位子打了一会儿。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,所以我很镇定,我的朋友可以作证。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,我毕竟问心无愧。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。”
“再说说我伪供的事。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,我没有谋杀山岸。他们不信,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。照他们所说,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,数字锁被砸坏了。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,包括我的,我共欠七百五十万日元。天哪!他们说对照了山岸的账本,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,他的借据不见了。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,由于月光暗淡,我看不清楚,拿错了。”
“另一个警探走进来,很得意地说,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,中村从家里浴室窗口,看到我急急忙忙朝山岸家的方向走去。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中村在看着我,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。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,有那只银箱作物证,又有我说过要杀死山岸的明显动机,这可是铁证如山,无可动摇。天啊!他们接着说,由于同情我,如果我招供,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,从此结案。他们如此说,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。我只好说,好吧!我承认是凶手。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,点香烟给我抽,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。他们要我画一张山岸家的平面图,我画了。根据他们的指示,我开始写供词。”
“写着写着,问题来了。第一,我不知道该说我用什么当凶器。有个警探像猫头鹰似的看着我,拉开脸说会不会是烧炉灶用的东西。我说对了,我用一块煤砸死山岸。这警探骂我笨蛋,说是从山上森林里面砍来的。他比划了长度。我说,噢!”
“是木柴。他说这就对了,问我藏在哪里。我怎么知道呢?就说藏在厨房的角落里。”
“他气得叫喊着骂我,说是在下雨天雨水一滴一滴漏下来的地方。我问是屋檐吧?他叫道:“对了!‘”警探把我带到山岸房子的后面,问我拿哪一根木柴当凶器的。我根本没有杀过人,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有个警探从柴堆顶部第二层拿了一根长木柴,问我是不是这一根。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,我不承认也不行,就说是的。这就是被当作我进行谋杀的所谓物证。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根木柴上没有头发和血迹。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山岸是秃顶,伤口往外流血很少。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。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,找不到指纹。”
“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山岸的。我根本没进屋子去,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,邀我到他房里去,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。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,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:既然我是客人,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。两人坐下后,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,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。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头。他们还添油加醋,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,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。我也只好承认了。”
“跟着,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。我说一下。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,喝问我到底打几下。我说六七下。但这又太多了,因为真打这么多下,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。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,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。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?我只好承认。”
“接着谈到银箱问题。什么砸开银箱、拿错了债据等等,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。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。我说左面的一个。他们要我再想想。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,一左一右,我就说右面一个。再者,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,我可就清白了;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,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。”
“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,警告我不得翻供,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。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,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,全是谎话,因此,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。”
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,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;但是,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,因此,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,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。
公诉人却不相信这第二份供词,认为上木欠了山岸一大笔钱,还不出,面临抵押物将被没收的威胁,谋杀动机是明显的。上木有时间作案而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。
中村古屋证明他看到上木走向山岸的房子,但没看到上木走进山岸的房子,因此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。
物证包括银箱和木柴。银箱上没有指纹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。警方调查报告里关于木柴上的指纹问题是这样写的:“问:你用什么敲打山岸的后脑?”“答:一根松木柴,像人们烧老式炉灶用的。”“问:那根木柴约有多长?”“答:大概有三十厘米。”“问:木柴在什么地方?”“答:噢,堆在山岸屋后的屋檐下面。”“问:你说你早知道木柴堆的地方?”“答:是的。”“问:你在作案后怎样处理那根木柴?”“答:我放回原处。”
“问:如果一起到木柴堆那里,你能指认那根木柴吗?”“答:当然,如果没人移动过。”“问:从尸体被发现以来,房子已被警方封锁,一切保持原样。”“答:当然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到了那里,能从柴堆里挑出那根木柴。”
接着,报告写了挑木柴的情况:“被告被带到山岸屋后屋檐下的柴堆处,那里有一堆约三十五层的木柴。他迅速地从顶上第二层认出一根来。他说:”就是这一根,就是我用过的一根。‘一名警探戴上手套,拿下那根被指认的木柴。被告也戴上手套,用右手接过木柴,左右挥舞了两三下,又朝下挥打了五六下。他说:“就是这一根,没错。’”在提供这一证据时,被告最合作了。”
原岛没有看过原始调查报告的全文。审判的日子快到了,他到拘留所去会见上木。上木表现得很有礼貌,原岛不大相信这个长着女娃娃脸的人会是凶手。他注视过上百双被告的眼睛,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看穿对方是否真诚。
“上木寅郎,我已经接受你的案件。如果你想得到正确的辩护,你必须全部实话实说。”
“当然,是的,我懂了。”
原岛问道:“你仍然要说你的第一份供词是伪供吗?”
上木立刻回答说:“绝对是伪供,我上了警方的当。”
“他们说你很合作,你甚至当着警探们的面指认出那根木柴。”上木摇摇头说:“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似乎在第二份证词里说了,警探们告诉我该说些什么。”“你对此能证实吗?”“当然。”“好吧,那么,我们就根据这些进行辩护。”
上木强调说:“原岛先生,我能证实我在供词是被逼出来的。”
“能证实?”
“是的。”
于是,上木从坐垫的事谈起。他说警方一定要他说,他进屋后山岸曾拿两只坐垫来坐,谋杀山岸后他把坐垫放回原处,以制造不是来客而是盗贼作案的假象。他只好承认是这么回事。他说:“其实山岸从未拿坐垫招待任何一个债务人。我去过他家好多次,没有一次坐过他的坐垫。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些到山岸家借债的人。”
“他为什么要把坐垫放在墙角里?”
“摆气派呗,懂吗?他的债务人没人坐过,因为坐下谈话时间会长。他强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,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待而要我们立即离去。我也不是说他不会拿坐垫给客人坐,只是不会给像我这种人坐。警探对这一点并不了解,就想当然认定我坐过山岸的坐垫。”
“你还有其他证据吗?”
“那只银箱,原岛先生,我不知道警方在哪里找到的。他们说是在有水的地方,我想起了两个池塘;但当我说在左边池塘时,他们骂我笨蛋,因此我告诉他们说是右边池塘。再说,原岛先生,我的债据仍在银箱里,这应该足以证明我没有谋杀他。
请你想想看,一个为取回债据而进行谋杀的人会拿错债据吗?警方说因为天黑,我拿了一个名字和我相似者的债据;但他们又说我稍后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烧毁了债据。这样的话,我必须身带火柴,对吗?我不是可以点燃火柴,看清楚我从银箱里拿出来的债据上的名字了吗?又怎么会拿错呢?不管怎么样,银箱上没有我的指纹,凭什么说是我偷的!“
“很好,还有什么?”
“有的,而且也很重要。那根被认作凶器的木柴,其尺寸与山岸头上的伤口符合吗?”
“你什么意思?”
“请听好。我看过法医报告的复印件。山岸后脑有一处头骨被敲得凹下去,伤口约有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;而警探逼我指认的那根木柴是三角形的,每一面约四厘米宽。原岛先生,我认为用这样一根木柴打三下是不可能造成那样的伤口的。
我的意思是伤口不可能那么平坦。凶手一定是用更大的凶器只打了一下,山岸就倒地死了。当然,这只是我的猜测,但也许你可以调查证实。“
原岛在归途中想,上木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,值得考虑。到了办公室,他看案宗的观点有了改变,印象也就不同。他的天平倒向上木一边。
有关坐垫的事,十来个人证实山岸从未拿过坐垫给他们坐过。看来警方只是根据常情,认为山岸会拿坐垫给任何来访者坐,从而认为是上木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盗贼作案的假象。
接着,原岛把验尸官的报告,给他一位当法医的朋友看,并征求他的意见。法医说:“我要说的只是设想。我看根据山岸致命的伤口情况,他是被一根八厘米以上宽的凶器敲一下就死的。奇怪,警方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。他们看不起我们,经常不把我们的报告当回事。”
原岛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好运。在法庭上,他请那位法医作证,陈述对伤口和凶器的意见。又请几个与山岸有往来的人作证,讲了有关坐垫的事。他还请三名讯问过上木的警探出庭,他们都说上木是自愿招供的。
——你是否对被告上木寅郎先生说过,“我们知道你杀死了山岸神,你逃脱不了;但是,如果认罪,我们会让你获得自由,请公诉人同意免予起诉?”
——证人甲:我从未说过诸如此类的话。
——在问讯过程中,你们是否曾用暗示办法,使被告承认他把坐垫放回原处?
——证人乙:不,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。
——你们是否曾使被告联想到木柴是他用的凶器?再者,你们是否引导被告挑出了现在法庭上出示的木柴,还说他用这根木柴从后面敲打了木岸的头三下?
——证人丙:当然不是,这都是他自供的。他自己挑出这根木柴。他说“就是这一根”之类的话,还挥动了几下,然后又说:“没错。”他很合作。
上木相当愤慨地对原岛说:“听到吗?他们说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,怎么能这样当众撒谎呢?”
三个月以后,因为证据不足,上木被裁定无罪。
裁决书罗列了下列理由:
1.作为凶器呈交法庭作证之木柴一根,最宽处四厘米。据验尸官与另一法医之证词,敲扁被害者头骨之凶器至少宽如成人手掌,八至九厘米(一著名医科大学专家在报告中持相同意见)。由此,被提供作为凶器物证之松木柴,并非谋杀凶器。
2.在此根松木柴上和山岸神之银箱上,均无被告指纹。
3.根据供词,被告取走银箱内二十二张债据中之五张,到离池塘约两百米远处的人寿保险公司操场上予以烧毁。留在银箱内有具名被告上木寅郎之债据。警方调查后曾假设,被烧毁的五张债据系他人所具。此人名字与被告相似。由此警方坚持认为被告因天黑未能看清而取错债据。看来似有其事,但被告律师坚持之见解也令人信服:如被告为真凶,取回债据乃首要目的,定会明确识认,决无取错可能。
4.审阅书面供词,未见有警方对被告进行逼供之迹象,但存有警方对被告进行欺骗和诱供之印象,可是这不足以使本法庭认为被告无罪。被告无法确切证明离开万园麻将馆到回该馆期间之所在和所为。疑点在于中村古屋作证称曾目睹被告在被害者居所附近出现。此点与被告第一份供词相吻合。
5.本法庭经慎重审核全部证词后之结论为:由于犯罪证据不足,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,特裁定被告上木寅郎无罪。
一年过去了,有一天晚上,爱在休息时看书的原岛直见,在一本英国法官詹姆?欣德的《无罪裁定研究》书里,有一起案例看得他脸红耳赤,气急心跳。
1923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船帆工厂的工人彼得?卡梅登被捕。他被控谋杀一富孀哈默沙太太,并纵火烧了她的房子。由于要钱用,卡梅登计划杀死她后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都偷走。他晚上7点左右到她家去,用五十厘米长的铁棍多次猛打她的脸,然后用他的皮裤带勒死了她,偷了一百五十镑现金和她房间里的一些珠宝,逃了。
为了毁尸灭迹,他又于两小时后回到她家,企图烧掉她的房子。他点燃了一只煤油灯,放在她写字台一本书上,灯的底部有一半超出书的边缘,灯就不怎么稳。
他又在地板上堆满废纸和衣服。如果灯跌下来,废纸和衣服就会烧起来,整幢房子将付之一炬。他知道一小时后,有一班火车将经过哈默沙太太屋后附近处,而每次火车经过时,都会引起房基和地板的轻度震动,这已足够使得放置的煤油灯震落地上。三小时后,整幢房子烈火熊熊。救火车赶到现场已无济于事。
不久,彼得?卡梅登被捕。他先供认,后又翻供。他被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而裁定无罪。
这是由于既无指纹又无客观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。他有许多朋友证明,在案发和被捕期间,他的言行没有不正常的表现。再者,在案发那天,他还乘火车到伦敦去玩,而在明知警方将对他进行调查的情况下,依然迫切地回到曼彻斯特。这些说法都对他有利。
卡梅登向警方招认,但后来又宣称是警方逼供的。法庭没有发现有逼供之事,确定供词可以作为证据。
然而,仔细研究供词,对照其他证据,却显示出有严重矛盾。在供词里,他说哈默沙太太最初开门时只开一条缝,他等她伸出头来时用铁棍敲打她的脸。两天后,他改供说她邀请他进屋。两人对面坐下,他乘她不备时袭击她。
他在什么时候袭击她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卡梅登不可能忘记这么重要的行动时间。
为什么他要说谎呢?两次说法的矛盾令人费解。
一开始,卡梅登说他用铁棍打哈默沙太太的脸只打了一下。两天后,他说打了两下。一个星期后,他说先用尽全力猛打了一下,当她头低下时又打了四五下。一位医学专家说,根据哈默沙太太的脸部骨头受伤的情况,说明她只挨过一下打。
那么为什么卡梅登后来说的与最初供词不同?记忆失误不可能。增加他打被害者的次数很可能对他不利,但又少有理由认为他蓄意作假。所有这些都造成对他初次供词产生重大怀疑。
在逮捕后,警方立即拿了些铁棍让卡梅登当面辨认。他说他用过的铁棍上应该有他的指纹。他似乎在想到底是哪一根,然后挑了一根出来,仍不肯定,用他的右臂量了一下这根铁棍的长短,最后说没错,这是他用过的那根。
被害者脸上的伤口比这根铁棍宽三倍。这就是说,这根铁棍不是凶器。为什么卡梅登要说是呢?真正的凶手会认不出他用过的凶器吗?看来,他指认一根没有他的指纹,又与伤口尺寸不符的铁棍,只是为了讨好警方、至于被烧毁的屋里是否有煤油灯跌落在地板上引起火灾,已经无法找到痕迹了。
法官宣布由于证据不足,被告无罪。
看完这起案例后,原岛感到似乎书中每一个字都跳出来打他一下耳光。两起案件十分相似。是巧合吗?不,不可能,因为太相似了。直感告诉他,上木寅郎看过这本书。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,上木在一家旧书店工作,结婚后才开面铺。
原岛打电话给一位爱收藏书籍的朋友,得知《无罪裁定研究》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文译本,更肯定上木会看过这本书。
原岛陷入沉思。在曼彻斯特案里,彼得?卡梅登指认一根尺寸有误的铁棍说是凶器。警方相信了他,就以此铁棍作为物证。上木做了同样的事,不过不是铁棍而是木柴。卡梅登在指认铁棍时,用右臂量长短,还说铁棍上会有他的指纹。上木在指认木柴时做了同样的事,然后使人相信他是受警方逼供和诱供的。
警探们曾说,上木很合作和友好。他们太得意了,以至被上木钻了空子。卡梅登和上木都在供词里一次次增加殴打被害者的次数,实际上他们各自只打了一次。
上木了解山岸的习惯,故意说山岸拿坐垫给他坐,是他行凶后把坐垫放回原处。上木还故意把自己的债据留在银箱里。反正山岸没有孩子,没有继承人,留着债据也不用还债,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了。原岛这个当上得真不小!
上木下落不明。被宣判无罪后,他以好价钱卖掉店铺和地皮,离开了东京。他没有来面谢原岛,只打来一个电话说:“怎么感谢你也是不够的。原岛先生,你是最卓越的律师。只有一点我很不好意思,你救了我,我却没有付你律师费。”
原岛已经完全明白了。他想,如果上木寅郎在交通事故中死去,这不仅是公正的惩罚,而且是上天的报应;不过,看来不像会发生这样的事。